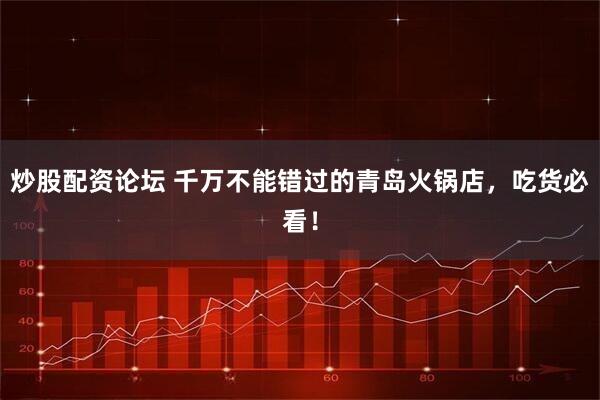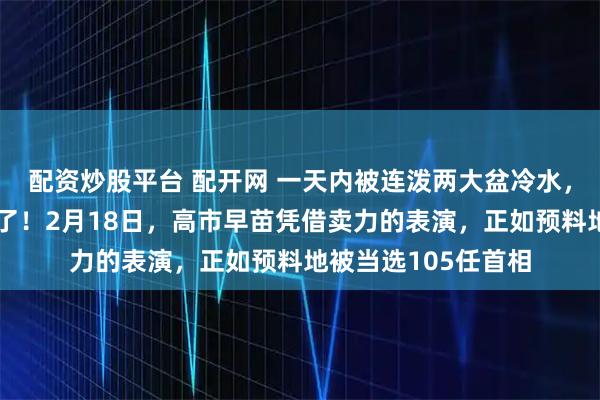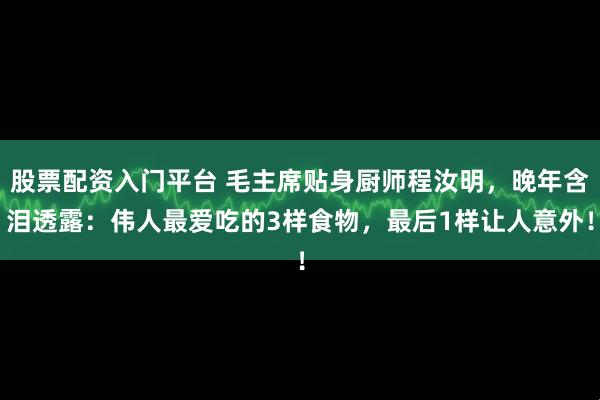
1984年4月的一个清晨股票配资入门平台,北京护国寺的小巷里飘出了阵阵肉香。邻居们循着香味走去,看见年近花甲的程汝明正用老式煤球炉炖锅。有人开玩笑说:“程师傅,这股香味儿简直把半条街都叫醒了。”程汝明抬头,轻轻笑道:“哪有那么神奇,只是照旧炖点红烧肉。”谁也不知道,这位眉眼慈和的老人曾在中南海掌勺二十二年,见证了共和国缔造者日常最私密的“一日三餐”。
程汝明出生在1925年,老家在山东蓬莱,七岁那年,他跟着爸爸漂泊到了天津。爸爸在码头上做伙夫,每天跟灶台打交道,虽然手艺不算精,但也让程汝明对火候有了最初的了解。那时候,天津到处都是流浪的人,他只能在小饭馆里刷碗换口饭吃。店里有个广东师傅,擅长做烧卤,偶尔会教他一两招。程汝明记性好,学得快,很快就学会了。解放后,天津的饮食业需要重新振兴,市里办了个“名厨讲习班”,程汝明因为能力突出,被破格录取。在班里,他从川菜、粤菜、淮扬菜一路学到法国西餐的基础知识,让同行们都羡慕不已。

1952年10月2日,外交部在北京举行了一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会议。为了这次会议,临时征用了地方上的名厨来帮忙。程汝明第一次来到会场,亲眼见证了全套国宴的流程:菜单需要考虑二十多个国家的口味,刀工、火候和上菜时间的误差都不能超过两分钟。客人刚放下刀叉,他就能判断出下一盘菜的温度要比室温高两三度——这种敏锐的观察力让总务处记住了他。会议结束后不久,中央办公厅通知他:“留在北京,等待调遣。”
1954年夏天,程汝明在中南海遇到了毛主席。那天上午十一点四十,毛主席刚批阅完文件,随口问了一句:“今天午饭谁来做?”旁边的一个卫士回答说,是新来的天津师傅。毛主席笑了笑,问:“叫什么名字?”程汝明紧张得手心出汗,但声音却很平静:“报告主席,我叫程汝明。”毛主席上下打量了他一番,然后摆摆手说:“那就做一碗家乡风味的红烧肉吧,别切得太小块,吃起来不过瘾。”毛主席说的“别切得太小块”,成了厨房里的第一条规矩,一直延续了二十二年。
程汝明的红烧肉和常见的不一样,他不用酱油上色。原因很简单:毛主席小时候在韶山帮家里照看酱缸,曾经看到发酵过程中长了蛆,从此就不喜欢这个味道。没有酱油怎么办?程汝明用老冰糖炒色,再加黄酒、葱姜,慢火炖煮三小时。油脂被逼出八成,肉皮还是那么胶原。端上桌,肉块两三两重,红润如枣,筷子轻轻一挑就断了。毛主席常自嘲:“这肚子是红烧肉养的。”身边工作人员听了都哈哈大笑。

专列上的军营条件很艰苦,但红烧肉却是必备的菜肴。1965年6月,主席前往安徽金寨进行调研,列车上的厨房只有不到三平方米,每次只能做两斤肉。程汝明临行前特意将带盖铝锅的一半锯掉,把手柄改成了竖耳,这样可以塞进煤炉里。炉火“叮咚”两声响起,车厢的晃动让汤汁溢出,他用帆布包住锅底,防止油滴烫坏监测线路。傍晚时分,主席夹起第一块肉,冲着他眨了眨眼:“小程,还是你做得最好。”
红烧肉让人觉得特别过瘾,而小鱼则像是心头的一抹温柔。主席不喜欢海腥味,但他特别喜欢河塘里的小白条、泥鳅和鲫瓜子鱼。1960年夏天,河北八里庄的水面浮青,警卫们在晚上休息时摸了两箩筐的小鱼。程汝明把小鱼洗净,加盐腌制半小时,裹上干粉炸到金黄,然后用剁细的朝天椒、蒜末和紫苏拌匀。凌晨一点,主席办公室里还亮着灯,程汝明敲门送上小盆。“放在桌子上吧。”主席头也不抬,批示写完后,拿起一尾鱼,咔嚓几口就嚼完了骨头。警卫们在一旁看得直咽口水。
1972年底,中南海的冬天特别冷,仿佛刀子割在脸上,湖面都结了冰。主席的咳嗽加重了,医生建议补磷补钙。程汝明想到了家乡湘乡的传统食俗——鱼头汤。可是北京不容易找到新鲜的大鱼,他向外交后勤部门求助,凌晨四点赶到密云水库,挑了半斤以上的大鱼头。鱼头劈成两半,用豆瓣酱炒香,先用大火烧开,再用小火慢炖,汤色奶白,鲜香带辣。主治医生尝了一口,连连点头:“不腥,入口不冲。”主席喝完后,咳嗽减轻了不少,声音虽然沙哑,但显得很满足:“这汤,暖胃又暖心。”

第三样让人好奇的爱好,就是主席对苦瓜的偏爱,这与他平时的饮食习惯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很多北方人一尝苦瓜,就觉得口感太涩,但主席却喜欢说,“苦能提神”。一次晚宴上,桌上摆着一道苦瓜炒蛋和一碗玉米面粥。程汝明忙于翻炒,主席突然招手说:“来来,这些菜别浪费了,你也吃点。”程汝明将红烧肉和几片炒鸡杂一扫而空,只留下了半碟苦瓜。主席一看,便夹了几片放进嘴里:“苦瓜不苦,革命才真苦。”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笑了。后来,后厨不小心将宫保鸡丁做成了苦瓜鸡丁,辣椒和花椒的辛香与苦瓜结合,竟别有一番风味。主席品尝后,不仅吃得干干净净,还要求再做一盘。
主席的饭桌上,节俭几乎成了习惯。1960年,国家最困难的时候,中央决定减少公务接待,领导们带头少吃肉菜。程汝明担心主席营养不够,除夕夜偷偷在葱花饼里加了点肉末。第二天,主席不动声色地把饼翻过来,笑眯眯地说:“小程,别为我破例,让群众先吃饱再说。”之后,他不再在主食里加肉,反而给主席准备了丰富的粗粮。高粱米、荞麦面、玉米渣轮流上桌,外加自制的酵母发酸汤,既美味又养胃。
程汝明有一套严格的保密制度,对外人绝口不提。毛主席的菜单是绝密文件,厨师必须做到吃完就销,连家人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。有一次春节回家探亲,妹妹好奇地问:“二哥,你给谁做饭呀?”他笑着摆手说:“别问,问了我也不能说。”直到毛主席去世后,家人才从新闻里惊讶地发现,电视上守灵队伍最前面那位面容沉痛的老人,竟是自家的哥哥。

程汝明记得1976年9月8日晚最后一次送夜餐。那天主席病得很重,却坚持吃稀饭配咸菜。程汝明想加点红烧肉,但被医务人员制止了。他只好把肉留给厨房的新学徒,自己站在门口,看到主席半睡半醒的样子。九日凌晨,哨兵敲响了紧急钟,程汝明赶到时,领袖已经离开了。他坐在走廊里,掌心还留有炊烟的味道。现在没有人再要求他切两三两的肉,也没有人再边嚼鱼骨边讨论诗词了。
从1977年到1978年,中央统战部找程汝明聊起了伟人吃饭的事。一开始,程汝明有点儿不想说,他想,主席不在了,他做的菜也该跟着封存了。后来,大家劝了他好一阵子,他才在内部的会议上讲了讲红烧肉、小鱼和苦瓜这三样菜。他一再强调,别把口味神化,朴实才是关键。直到1984年,他家街角那阵子飘出的红烧肉香被邻居闻到了,他才偶尔接受地方报纸的简单采访,随口加了一句,说:“味道是生活的一部分,记忆越真实,味道就越香醇。”
程汝明成为“领袖厨师”后,依然没有停止钻研。他常说:“厨师没有捷径可走,刀工、火候、细心缺一不可。”1992年,广东举办“改革开放十周年国宴示范”,邀请他担任技术顾问。他到厨房的第一件事,不是指手画脚,而是挽起袖子切了一块三层五花肉。年轻人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,偷偷说:“他切出的肉条像尺规画的。”程汝明听到,呵呵笑道:“那是多年练习出来的手感,别急,慢慢来。”
退休后,他拿起旧笔记,可不是什么菜谱,而是那些藏在角落里的小故事——粮油的供应、食物的保鲜,还有那火车上的灶台怎么改的。原本以为写个十万字,结果翻出来三十五万字。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看了他的笔记,直夸:“这些细节太实诚了,比书上的资料还生动。”他只是笑了笑,说:“我只是把事情原原本本记下来,留给后来的人参考。”出版社两次想让他给故事添点花花绿绿的色彩,他却坚持只删不改:“一添就走样了。”最后,《围桌记事》只在小圈子里流传,知道的人不多,但口口相传,它还是有了自己的声音。

毛主席特别喜欢吃辣椒,他说辣椒能提味醒脑。辣椒能解热提神,出汗后更舒服。毛主席从不浪费辣椒籽,有一次在西柏坡开会,苏联代表对满桌辣菜望而却步。毛主席把盆辣椒摆在桌子上,说:“来尝尝,这是咱湖南味。”外宾红着脸只吃了一口。晚会结束后,碗盆里的辣椒全吃完了。警卫员说毛主席把人情世故都放在辣椒里了。
程汝明认为,食物和政治是两码事——食物关乎日常生活的身体和情感,而政治决定国家的方向。正因为如此,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厨房的独立空间,即使外面的环境再动荡,也保持菜刀砧板声的平稳。1974年,有人建议为最高领导人设立一个品尝小组,程汝明婉拒说:“能吃、爱吃就行,别让饭桌也开会议。”主席听后爽朗大笑:“小程有理,吃饭就吃饭,不议事。”
程汝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,厨师得明白“吃得开心”和“吃得健康”的区别。毛主席晚年食量不大,程汝明就用小火慢炖肉类,换成了茶油和花生油交替使用,这样能减少胆固醇的累积。医生看到化验单上各项指标都挺稳定,大为惊讶。程汝明解释说:“油类品种多,营养才能均衡。”这种见解在那个年代显得挺超前的,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,营养学界才开始全面提倡这种理念。

临近2001年春节,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纪录片《名人与厨房》,希望邀请程汝明参与。他听完后客气地谢绝了邀请,只留下一封简短的信给片方:“请不要把日常家常菜拍得像是神秘的大宴。”尽管如此,制作团队还是安排了他与年轻主持人一起泡茶的片段。在拍摄的间隙,主持人好奇地问道:“老程,你这一辈子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?”程汝明想了想,回答说:“是我长时间翻动铁锅时手上留下的茧,还有一次毛主席对我说‘不要切得太小’时那轻轻一挑眉毛的瞬间。其他的事情,都渐渐淡忘了。”
在2014年的那个宁静夏夜股票配资入门平台,程汝明老先生安详地离开了我们。市里为他举办了一场追悼会,缅怀他的生平。在吊唁簿上,有一行特别显眼的字迹,那是附近小学的一群少先队员们用稚嫩的笔触留下的:“程爷爷做的红烧肉最好吃。”在那行字的黑白墨迹间,一颗关于美味的种子,悄悄地生根发芽。

倍悦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散户在哪个证券开户最好 一夜防空就烧掉8000万!欧洲援乌已力竭,还要砸钱打远程消耗战?
- 下一篇:没有了